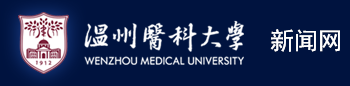
浙江在线12月5日讯(记者 梁建伟 叶小西)“你看,这是我曾经差点毁容的脸,现在是不是已经看不出异样了?”
记者:“生长因子”是什么?您能用最简洁又形象的语言,给大家科普一下吗?它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又有怎样的作用?
李校堃:你可以这样去想象一下:壁虎的尾巴断了,为什么能再长出来?这是因为有一种因子能促进它再生长。其实,在人体内也有一种神奇的细胞因子——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它能治疗溃疡和加速损伤组织再生,让损伤的皮肤得以较完美修复。我们把这种因子做成药物,用于重大灾害性创伤、国防战伤等的救治。
最早是美国科学家发现了“生长因子”的存在,但我和团队成员坚持不懈研发,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把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开发为新药的国家,比日本早4年,比美国早6年。并且,我们还发现了“生长因子”有利于治疗糖尿病多种并发症,如糖尿病溃疡、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
去年,我们又有了一项重大发现,论文在《Nature》杂志上发表后引起国际关注。这篇论文解析了人体“抗衰老蛋白αklotho-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1c (FGFR1c)-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23 (FGF23)”三元复合物晶体结构,证实了FGF23是调控衰老及老年相关疾病的关键靶点,能指导未来抗衰老和代谢性疾病药物的开发。
现在,我们已研发投产“贝复济”“扶济复”“艾夫吉夫”3个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一类新药,这也是国际上第一个系列“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一类新药。实验表明,系列新药能促进皮肤血管新生,促进皮肤神经及汗腺毛囊等皮肤附属器件功能修复,进而主动促进创面修复,帮助伤者缩短创面愈合时间,减少疤痕。这是创伤修复的新理念。截至目前,一类新药在全国5500多家医院服务患者超6500万人次,另有4个药物获批临床试验,拥有45项国家发明专利,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谈家桢生命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转化医学突出贡献奖等各类奖项。
记者:当初您是如何开启“生长因子”揭秘之旅,与它真正结缘,又是怎样一种机缘巧合?
李校堃:1992年,我师从暨南大学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林剑教授,开启了“生长因子”研究的征程,也就是在这一年,一场意外,让我更加坚定了要把这条路走下去。
有一天深夜,我从广州图书馆骑着自行车回寝室,校门口外正在挖水沟,只有一块铁板架在上面。我经过时不小心骑到沟里去了,沟里有很多锋利的石头,我的半边脸多处挫伤,鼻梁、颧骨等5处穿透伤。送到医院后,初步估算需要缝合30多针。我当时想,缝30多针,脸就要变成鞋底了。当天晚上,医院里没有缝合的医生,值班医生就让我先回去,第二天再去缝合。
那一晚,我疼得根本睡不着觉。在床上辗转反侧,无意间想起了放在冰箱里的几瓶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喷雾剂,这是导师要我带去进行动物实验的试剂。
我突然想到,既然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可以修复创面,是不是可以用在自己身上?可是,当时学界对“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的研究仍停留在动物实验阶段,尚未进行过临床试验。
我拿起喷雾剂,放下,拿起,又放下……我当时心里也非常害怕,万一用了留下伤疤怎么办?会不会长出肿瘤呢?犹豫再三后还是放回去了。
但晚上实在睡不着,于是就起来决定试一试。第一次只喷了一点,因为害怕,没有再喷。结果躺在床上还是睡不着,于是横下一条心,往伤口上又喷了很多。
没想到喷了一会儿后,伤口就不大疼了,第二天就结痂了。第二个星期结痂脱落,再过一周后伤口痊愈,也没有留下明显的疤痕。
还有一次,我的左手腕被一块铁板烫伤,都见到肌肉了,也是喷了“生长因子”,现在基本上看不见伤疤。
正是这几次“以身试药”的经历,让我觉得“生长因子”太神奇了,从而坚定了加速研制新药的决心。
沉下心来 携手攻坚克难
记者:“生长因子”研究非常难,国外科学家都望而却步,您是怎样实现突破的?
李校堃:我从事“生长因子”研究近30年,前15年就做一件事——如何把“生长因子”提炼出来。
这个事很难,1万头牛的脑垂体,只能提炼出1克,成本太高了,这条路行不通。后来有了基因工程,我就把基因技术用到提炼上来,大大降低了成本。
这是一个巨大的技术突破,从此以后的10多年,“生长因子”这项研究正式进入生物医药研发阶段。
“生长因子”作为药物应用从来没有先例,不少西方学者认为“生长因子”有成瘤和多度增生风险。那时候我在国际会议上作关于“生长因子”的研究报告时,经常受到一些学者质疑,这也成了我科研生涯中最艰难的日子。那个时候,我告诫自己,一定要沉下心做科研,用实践来回应质疑。
记者:为了采集关键的实验数据,您常常席地而睡。听说,有一次深夜太困了,便躺在地上睡着了,醒来发现整个人都泡在水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李校堃:那次做实验实在太困,就直接躺在地上睡了。不巧那天实验室突然停电,冰箱里的冰块融化了,流出的冰水将我从睡梦中冻醒,醒来时发现整个人都泡在了水里。
我们搞研究的总是这样夜以继日,一个月吃睡都在实验室,是常有的事情。有时候,为了做一个关键性的实验、等待一个关键的数据,会一整夜不合眼;有时为了一个议题,一个好的想法,团队成员会探讨至凌晨。
记者:您和学生在一起的时候是非常享受的,不知道我的猜测对不对?
李校堃:15年来,我和团队成员把温医大东北角这栋不熄灯的实验室当成了家。因为白天要忙于学校的行政事务,我经常把研究时间集中在晚上。在这里,我常常待到凌晨才会离开。
印象最深还是夏天,实验室里的空调常常不好使,我们一群人在里面做研究,热得满头大汗。我记得刚从广州来到温州时,这个实验室里只有十几人,现在已经有上百人了。我的很多学生也在温州成了家,他们也培养出了博士生、硕士生……大家都在这里扎了根。
记者:听您的学生说,您除了爱待在实验室,还喜欢跟他们去撸串吃烧烤?
李校堃:对。每次在实验室一待就已经是深夜了,常常会觉得饿,我的团队中有很多80后、90后,这群年轻人爱去小食街撸个串。我呢,除了填饱肚子,最重要的是想换个轻松的环境和年轻人多聊聊天。我们有很多新的发现也是在路边摊撸串时“聊出来”的。和他们聊天,也是我放松和调节自己的一个重要方式。
记者:现在听来,您真的很忙,但看您的状态,又觉得精力特别旺盛,您是怎么做到的?
李校堃:每次看到病人使用我们研发的一类新药痊愈后,我和团队成员都高兴得不得了。科学研究让我们收获了很多快乐,团队成员之间也建立了兄弟般的感情。因此,我们总觉得有使不完的劲,只想着如何把工作做到极致。我的梦想就是把中国的“生长因子”研究做到全世界最好,并一直保持领先。人一旦有了激情和梦想,就不会觉得累。
记者:您是陕西人,小时候大部分时间在长春读书,大学和深造阶段均在广州。为什么会选择来温州进行“生长因子”的研究?
李校堃:2004年,瞿佳教授将我引进到温州医科大学后,我就深受“温州精神”感染。“温州精神”是勇于创新的精神,温州人敢把别人看不上的东西,做到极致,比如当年的纽扣、拉链,这和我们做“生长因子”研究有相通之处。
记者: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您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接下来,您和您的团队有哪些目标?
李校堃:在“生长因子”的研究领域,我们已经领跑全球了,但“生长因子”的探索之旅依旧漫长。
过去30年的研究,只是“生长因子”研究的冰山一角。好比小麦传入中国时,我们只知道它可以吃,但不知道怎么吃,怎么变着花样吃。但现在,我们的面食可谓五花八门,“面面”俱到,“生长因子”也是一样。如今,我们有了更好的科研条件,有信心做出更多成果。
生物药物是一个高投入、高产出、高回报的产业,一般需要10年到1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如今,我和团队的科研项目在珠海、广州、上海和合肥都有了产业化基地,但我更希望能在浙江、在温州加快打造一个以“生长因子”生产制造为主体的产业化基地。希望温州在营造生物高技术产业落地的环境上,能更有作为,希望“生长因子”在温州这片土壤上开花、结果,长成参天大树。我们也期待通过产、医、研、资协同创新,推动一批再生医学新技术、新产品、新策略的加速成熟和产业化,进而推动温州产业格局的升级。

媒体链接:
扫一扫在手机打开当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