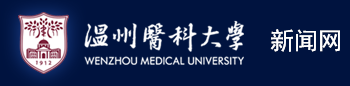
清明前夕,从温州医科大学毕业30年的顾永斌医生,再次回到母校。这天,学校里正在举办感恩追思会,1000多名医学生到场送别5名“大体老师”。他,是来接父母“回家”的。
骨灰盒前,一个纪念水晶球静静地立着,上面写着:生命如花、感恩捐献。
顾永斌不禁想起,当年自己迈进医学校园时,父亲的叮嘱:多学一点、多掌握一些,去治病救人。四年前,父亲顾润德病逝,他在临终前选择捐献遗体供医学研究。一年后,他的母亲唐莲芬因突发心脏病去世。夫妻俩作出相同的选择,在儿子的学校里“重逢”。
慈爱的父母亲
“孩子,这是好事,你尽管去做吧……”顾永斌回忆起在母亲住院的最后时光里,她还是像以前那样柔声细语。正如一年前,长期患有帕金森病的父亲,在难得的清醒间隙,对于顾永斌问起的关于身后事的打算,也是坚定地点头。“其实老人也不太懂什么是遗体捐献,他们就是一直支持我、相信我。”提起父母,顾永斌湿了眼眶。学医的顾永斌,十几年前就填写了遗体(器官)捐献登记表。他记得,在校期间上人体解剖课的时候,一个班的学生只有一名“大体老师”。“动手解剖的机会太少了,这其实不利于医学生对于人体解剖结构的学习。”
“大体老师”紧缺,是医学院校长期面临的普遍问题。在顾永斌看来,哪怕是微薄的力量,也能汇聚成为推动医学进步的星星之火。
填完登记表后,他把自己的想法和决定告诉了父母。“他们没表示反对。”
后来,他的父亲患上帕金森,治疗了5年多,没什么效果。眼见着父亲的记忆一点一点衰退,直到不认识每一个人。“还有很多疾病是现代医学无能为力的。”于是,顾永斌试探着询问父亲,是否愿意捐献遗体供医学研究,父亲当下就同意了。
两位老人成为“大体老师”的三年里一批又一批的医学生们,在他们的躯体上进行模拟手术训练,了解人体内部结构、认识神经和血管走形,划下自己的手术第
一刀。如今,“大体老师”退休了,顾永斌打算带父母海葬。“回归自然,这是他们的心愿。”
不被理解的选择
顾润德和唐莲芬夫妇,不仅捐出了遗体,还捐献了角膜,帮助了4 人恢复光明。
但作为儿子,顾永斌也遭受了巨大的压力。至亲们不理解,甚至一度断了来往。很多人反对,他们问我为什么不跟他们商量,自作主张。
在传统的观念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对于遗体捐献这件事来说,如果活着的人不支持、不理解,就很难操作。因为遗体捐献需要生者去施行。”温州医科大学人体科学馆副馆长杨新东坦言,在每年的遗体捐献者中,都会有个别家庭因为受到周围的阻力而选择放弃捐献。“达成理解的过程,是不容易的。”
吕金桥,也是今年退休的“大体老师”之一。当他把捐献遗体的想法告诉家人时,没有人能接受,也不同意。他告诉妻子林华英:“遗体捐献可以让更多的人走出痛苦,让更多人的生命得以延续……”在病重之际,最终在妻子的陪同下,吕金桥老师签下了遗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表。
另一位“大体老师”吴岩友,临终前叮嘱女儿:“我签过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表,做人要说话算话。”他的女儿徐慧君还记得,村里乡亲都不能接受,但自己答应过父亲,要遵从他的遗愿,为此也遭受了一些非议。
在感恩追思会上,徐慧君和丈夫、女儿,专程从杭州赶来,接父亲“回家”。她说:“父亲本着再为社会作点贡献的善意,作出了生命的最后一次选择。我希望这种善良的品质能够传递给孩子。”
生命的芬芳
向“大体老师”献一束花,默哀、鞠躬、致敬,这是医学院校解剖课每年固定的开学第一课。
温医大眼视光专业的陈宇泉说起自己第一次拿起手术刀,在“大体老师”身上一层一层解剖时,不小心刺破了脏器。“我马上调整了拿刀的力度和手法。”
“宁愿医学生在我身上划上千刀万刀,也不愿在患者身上划错一刀。”“大体老师”们无言,却甘心成为每一个医学生的第一名“患者”。
据温州市红十字会数据统计,2008年以来,已有185人在离世后捐献器官,115人成为“无语良师”,4.8万多人加入志愿捐献登记者的队伍中。
在温州医科大学的人体科学馆里有一面写满遗体捐献者的姓名墙。他们中有教书育人的老师、有扎根一线的工人、有救死扶伤的医生、有勉为公的党员干部……馆内两侧放置着书桌,医学生们正在潜心学习。窗外的阳光照进来,一个个闪亮的名字,明媚而温暖。在未来医生的内心里,一颗敬畏生命、刻苦学习,为消除人间病痛而持续努力的种子开始吐露新芽。
扫一扫在手机打开当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