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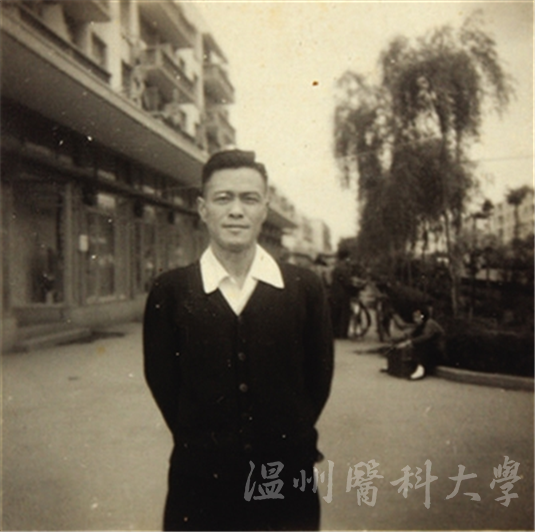
在“比户书声”的瑞安城关,凡是上了年纪的都曾听说过我的父亲项棣荪的名字。他是瑞安城里最早的西医之一,瑞安医院放射科创始人。
父亲1919年出生于瑞安城关南堤街的书香门第。兄弟四人,大哥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早稻田大学,取得双学位,二哥毕业于南通农学院,三哥毕业于北京华北政法大学。
父亲自幼聪颖好学,瑞安中学初中毕业后,进入之江大学附中,旋以优异成绩考入国立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刻苦钻研各科知识,成绩优异,掌握了X光透视及仪器使用、修理校正等技术,颇得教授们的赞许,认为是一位不可多得的高材生,毕业后,应聘为医学院附属医院(现华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医生。
1946年,父亲返乡,被温州瓯海医院(现温州医科大附属第一医院)院长林镜平聘为医务主任兼外科医师,医文职业讲习所主任。
1949年初,父亲从温州回到瑞安,先在自家开诊所,其间被瑞安中学聘为校医兼生理卫生课教师,同时被瑞安县人民医院聘为特约医生。1951年瑞安县政府任命他为瑞安县人民医院医疗股股长兼内科医师,1954年任副院长,主管业务,参与了瑞安人民医院的创办。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瑞安还没有X光机等医疗设备。父亲和王时望医师等一起想方设法分别从董若望医院(今温州三医)借来30mA的X光机头,从瓯海医院(时称温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借来30mA的X光机身,然后装配调试成X光机,成为瑞安医院的第一台X光机,从而大大提高了当地医疗诊断率。那时他常常白天看病,晚上透视,拍X光片,经常工作到深夜。
由于受过高等医疗专业教育,加上不断跟踪国际先进医学知识,父亲治愈许多疑难病症,名气很快就传遍温州、瑞安,慕名而来的病人络绎不绝,一举成了瑞安医界最有权威的医师之一,被选为瑞安县一至三届人大代表,瑞安县一至三届政协常委。
父亲虽然在社会上很有名气,但从不收受病家礼物。他常对朋友说:“做医生应该扎扎实实地干,为病家解除痛苦,多读医书,使医术不断进步,自觉注意医德,以免被人议论。人言可畏,极应戒之,慎之!”
在家开诊所期间,他从来没有收费规定,病家愿意放多少钱在桌子上,由病家自己定。经济困难的病家若拿不出钱也不要紧,甚至有时还送药给病家。除了坐诊外,对走不动的病人还经常出诊。一位乡下的木工师傅得了伤寒病,很危险,他采用当时最好的救治手段抢救成功,因为木工师傅经济困难,并没有收医药费。很多年以后,木工师傅还专程来道谢,但我父亲却早已离开人世。
兼职瑞安中学校医并兼生理卫生课教师与被聘为瑞安县人民医院特约医师时,我父亲均没拿报酬,遇疑难病症或外科、妇产科急诊手术,都请他会诊或主刀,随请随到,从不摆架子。
1952年,省卫生厅来瑞安县人民医院调查医院的制度建设,发现原始病历(包括初诊、复诊)的记载、查房制度的执行、三班制、门诊值班等制度和执行很齐全到位,档案完整,高资历医生较多,非常满意。因此,瑞安医院在全国县级医院中排名第二,仅次于广东梅县医院,这与当时医院领导的重视及负责医院业务工作的父亲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
1962年夏天,副霍乱传染病在瑞安县流行,父亲全身心投入指挥防治工作,还连夜编写防治副霍乱病的宣传资料,紧急举办医生、护士及防疫人员学习班,进行专题学术报告,在自身罹患肺结核病、肺气肿并伴咳血的虚弱情况下,带病坚持六个小时讲课,做完报告回家后,就大量吐血,在病床上仍念念不忘副霍乱病的防治工作。
他非常注重学习先进医学知识,通过同学定期从国外寄来医学外文杂志,或者自己到上海外文书店买来医学书籍,每天夜里看书到深夜,不断地学习国外先进的医学知识。
据医师回忆,1962年副霍乱流行时,一次内科医生对一病人大便副霍乱杆菌培养四五次,有一次是阳性的,就按副霍乱治疗。可是经过20多小时的抢救,病人没有好转,甚至昏迷了。后请外科医生会诊,外科医生想起我父亲说的话,根据病人的临床症状,考虑为急性节段性出血坏死性肠炎,并建议手术治疗。当时国内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临床更没看见过,大家半信半疑。与家属沟通后,同意手术,打开一看,确为小肠一段段坏死出血,诊断完全正确。父亲医术之高超可见一斑。
父亲身材魁梧,仪表堂堂,声音洪亮,在我们眼中他是位精力非常旺盛的人。实际上他患有肺结核、肺气肿、支气管扩张等顽症,自身肺功能代偿不全、呼吸较常人困难,每每看了病人后,常常咳嗽不止,气喘难受,但工作起来常常会忘记自己的身体。
在家中,父亲对我们要求很严格,从小就要养成卫生的习惯,吃饭前必须洗手,吃饭时必须戴围兜,以免弄脏衣服。后一点让我为难死了,因为我的同学都没有这个习惯,有时同学来,我正在吃饭,给同学看见,自觉太难为情了。而这事,不久以前,还有人谈及呢。
父亲对我们的要求虽然很严格,但留给我的印象却又很温暖,小时候淘气犯错误,父亲会让我们自动走到他面前认识错误,并让我们自动取来特制的“戒方”,自动伸出手让他打,犯了错误就要受惩罚,经历了几次教训,慢慢地明白了事理,学会了自律,“戒方”也就远离了我们。
父亲的肺结核病灶接近血管,吐血的时候,是一大口一大口地吐,那时候条件差,只能拿旧报纸擦,我们站在边上心疼啊,但又无能为力。由于肺气肿,他无法正常呼吸,经常用大拇指顶住喉咙(大概可以稍微好受一点),喉咙被压得一大块青紫。他的身体每况愈下,终于1964年11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弥留之际,父亲还嘱咐家人把自己所有医学书刊数千册(大多数是外文书刊),全部捐赠给瑞安人民医院(后来装了三大板车),留给后人阅读参考。
原文链接:
扫一扫在手机打开当前页